

读《三十六陂烟水》
文、图/廖博思
春天了。
广州的春天并不太美好,反复的天气,永远干不透的衣服,呼吸间一股闷闷的霉味……我是这么厌烦广州的春天,但当我在异地他乡,看着满园春色的时候,我又如此想念它——这种情绪是复杂的,它是外国人口中的“思乡病”,homesick,是韦应物“故园眇何处”的感触,也是游子远走的惊鸿一瞥……
《三十六陂烟水》里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种幽微的心事。
这是一本写满了乡愁与他乡见闻的华侨手稿,书名出自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共分三辑,第一辑“落日楼头”,抒写海外人生;第二辑“白头想见江南”,描摹故国所忆所见所感;第三辑“坐看云起时”,包括读书笔记和议论性文章。作者刘荒田是美籍华人,他生长于侨乡台山,又在海外生活多年,因此,他的文章中总是透露着一股散不去的
“乡愁”。
自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在华人中流传,“乡愁”便成了华人表达对故土情感的词。余光中把乡愁比作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他在这一头,母亲、新娘和大陆在那一头。而对于海外游子来讲,乡愁是他乡与故土相似的曙色,童年关于“寿星公”炼乳和鸡蛋的回忆,姐姐结婚时塞在书包里的喜饼……双脚站在他国土地上,听着孩子们稚嫩的歌声,思绪如无根浮萍般漂荡——他们在太平洋的这一头,祖国在太平洋的那一头。
根,属于华人共同的执念。
以前读华侨史,恢弘的叙事中总能看出一种华人对故土的执念,体现在对家乡的建设上,体现在金山轨道的血汗上,体现在战争时一串串悲壮的数字上——很宏大,但也很缥缈,总感觉看见了,又似乎没看懂;读《三十六陂烟水》,能看到的是个体更具象的执着,对故土的怀念抑或是对童年的追忆,对异国新奇趣事的见闻抑或是尝试融入当地文化的窘迫。
通过阅读本书,不难看见记忆中海外华侨的“乡愁”内容正在改变。新一代的海外华侨,他们往往有高学历,跻身中产阶层,有能力到中国出差或度假,同时高新科技的诞生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回国对他们来说变得容易,亲朋好友的联络只需要打个电话,物理距离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换个角度说,他们对于故土的“乡愁”已经不再依托于物质层面了。
但是“乡愁”仍在。
又如本书作者刘荒田,去国三十六寒暑后,依然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暂住者”,他“投入本地的事务,维护环境,参加各种听证会和投票”,努力让自己像一个旧金山人,或者说做一个旧金山人,只是为了“向因为我们不投票不参加各种公民行动而对我们掉以轻心的政客们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他拿着美国护照,但在精神和文化上,仍把自己视为客人,而当他回到阔别的家乡,听着陌生的乡音与他分享故土的点滴,他又觉得惆怅,“我点头赞好,也暗里怀着遗憾,为了我的记忆和榕树没有牵连;入秋以后依然油绿的叶子,在风里的诉说我难以明白”。
新一代华侨的乡愁,似乎总是有一种苦涩。这种苦涩源于一种精神上的不伦不类:自己既不是外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有着华人特有的对“根”的执着,又热衷于将自己融入所归化的“第二故乡”的文化。“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说到底,“乡愁”这个问题好像是没有答案,或者没有结果的。远离故土,出走他国的海外华人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融入他国主流社会的目标,可能要由他们的下一代、二代甚至更后辈的才能完成,而即使这样一代代完成了思想上的“归化”,华人血缘中带着的对“根”的执着又会驱动着他们回到故土溯源——如此,便完成了“落叶归根”的闭环。
乡愁啊,太深沉,太苦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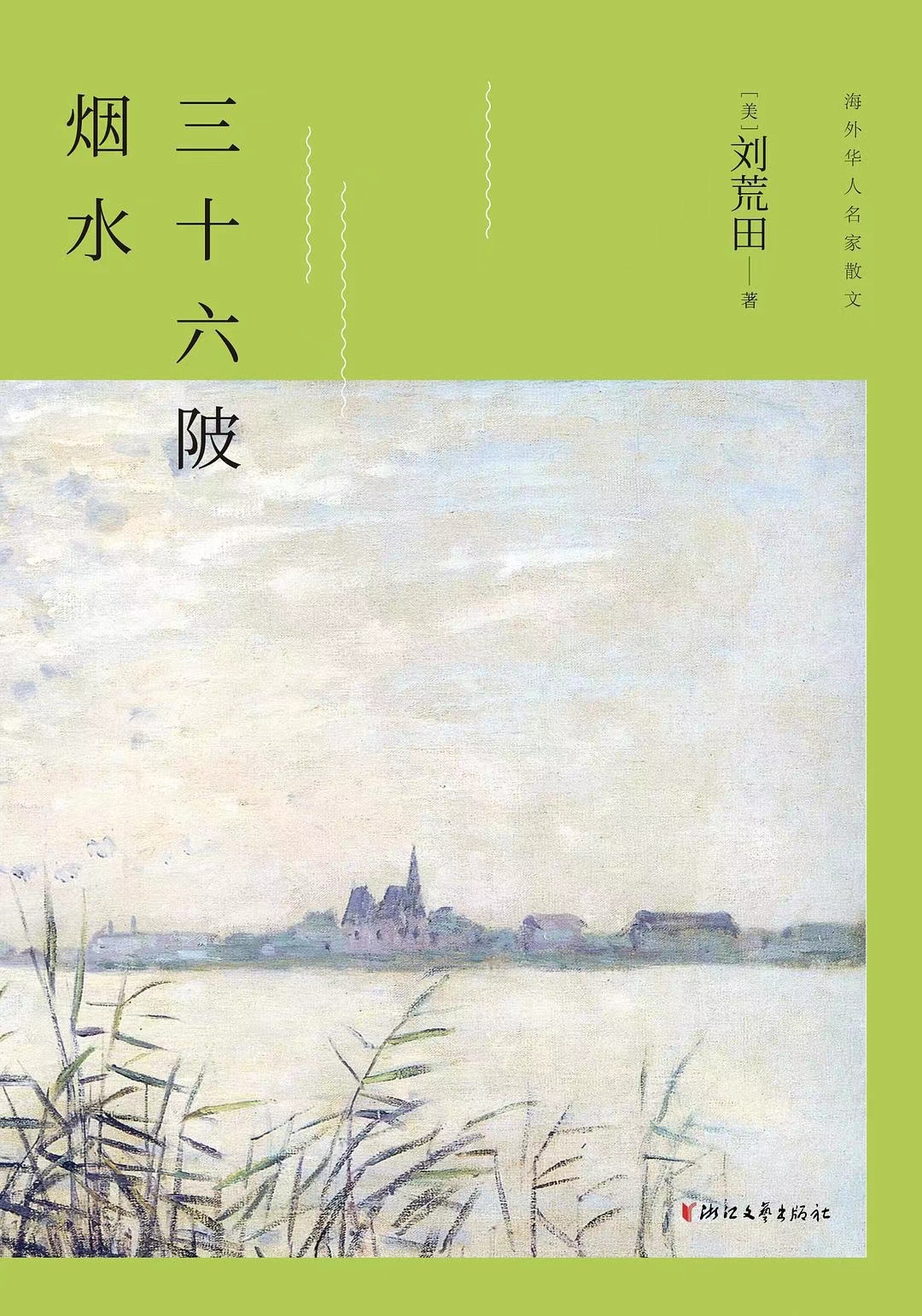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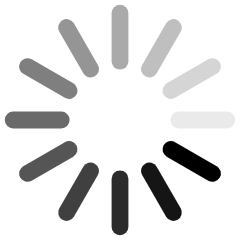 继续访问
继续访问